投稿:薛小妹啊日期:2023-09-13 09:15:23人气:265+
朱自清的简短评价
《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接下来具体说说朱自清的根本缺陷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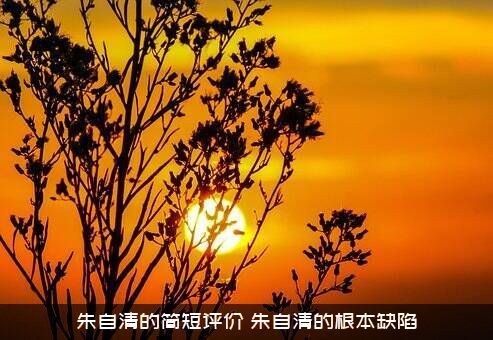 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
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
“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提升。
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
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
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
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
”
(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
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
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
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
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
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
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
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
“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提升。
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
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
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
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
”
(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
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
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
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
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
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
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
朱自清的散文语言优美清新,如《荷塘月色》,感情真挚细腻如《背影》,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感觉,他和鲁迅、周作人并称为现代散文三大家,其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让人钦佩的。
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散文“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朱自清先生以其“真挚清幽的神态”屹立于“五四”散文之林;他的散文韵致无穷,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读之令人心醉沉迷。《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历来一直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
在“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极一时之盛”“绚烂极了”的散文百花园里,有周作人的隽永,俞平伯的绵密,徐志摩的艳丽,冰心的飘逸,而朱自清先生则以其“真挚清幽的神态”屹立于“五四”散文之林(钟敬文《柳花集》,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初版),他的散文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关于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评价,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素伯说散文集《背影》给人以“芳香的迷醉”,叶圣陶说〈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匆匆〉等文,“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不怎么自然”。
这几篇散文“论文字,平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旅美学人夏志清,则认为〈荷塘月色〉这些文字“‘美’得化不开……读了实在令人肉麻”。
2 余先生在该文中还有一段关于现代审美的发挥—— 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在视觉经验上,不该只见杨柳而不见起重机。
到了70年代,一位读者如果仍然沉迷于冰心与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着他的心态仍然停留在农业时代,以为只有田园经验才是美的,所以始终不能接受工业时代。这种读者的“美感胃纳”,只能吸收软的和甜的东西,但现代文学的口味却是兼容酸咸辣的。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文学欣赏与批评要有现代感的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应该看到,研究者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放、方法的多样,都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尤其是海外台港华人学者是大陆文学研究的有力促进者、极大推动者。他们既有中国传统学问之根基,又有西洋文化之训练,思路开阔、理性思辨力强,对世界优秀文学之优异处有深切体悟,对世界优秀文学理论之大势有精深把握,因此在研究中国文学之时,能在中外文学文化的宏观背景上,能在现代世界的学术基点上,作出深刻的理解,道人之未道,往往能产生震聋发聩的反响,引导大陆学术界之潮流。
仅从文体而论,最突出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叶维廉的新诗研究和余光中的现代散文研究。虽然他们并不局限于上述领域,但确在小说、诗歌、散文研究方面取得了超出大陆学界的成就。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80年代学术界的影响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是他,发现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师陀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并引发了大陆历久弥新的“张爱玲热” 、“沈从文热” 、“钱钟书热” 。
是他,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并冲击了大陆学术界的价值观念;新诗研究名家辈出,但在学理的层面上对新诗的特质和新旧诗的区别作出了深入探讨的,当首推叶维廉的《中国诗学》;跟上述两位较纯粹的学者身分不同,余光中主要是一个作家,他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称之为第三者插足,虽只偶尔为之,但他“插” 得也够深的。
比如他对朱自清散文的批评,虽只是他众多评论文章中的一个篇幅不大的成果,但其胆其识,已在一般学者之上。
上述夏、叶、余三人,批评活动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视野和理论极具“现代感” 。所谓“现代感” 是一个大家都能意会但界定并不精密的说法。
我的理解是,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感” ,大致是说,不论研究中外古今的什么文学现象,都能以中外优秀文学为宏观参照系,都能守住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 ,并站在现代世界文化文学的基点上予以审视。这并不是强制性地用今日之标准规范前人,也不是牵强地要前人的创作符合今日之审美趣味,而是说从现代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整体观照。
尤其是对与我们今天基本上处于同一文化背景的20世纪文学,对其进行现代性审视,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现代感,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的孤独蕴涵的现代人生体验,就无法从郁达夫的颓废**文字中读出其反封建倡人性的现代价值,就无法从李金发的死亡之诗中看出其超越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感慨的现代知识分子情怀,就无法从丁玲的“莎菲” 中看出站在现代人格平等观念上的女性对男性的审判;如果没有“现代感” ,夏志清“发现” 不了张爱玲、钱钟书,叶维廉发掘不出新旧诗的异同;如果没有“现代感” ,余光中批评不了现代白话散文的“大师”、“宗主” 朱自清的根本缺陷。
介绍完余光中先生切实中肯而又不同凡响的看法之后,还有一串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余先生而不是大陆学者发现了朱自清散文中的瑕疵?为什么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对朱自清只有推崇而没有责问?为什么朱自清在我国读者中有这么长久的魅力?原因当然很多。
简单说来,大陆的现代化步履过于简单和缓慢,人们的心态也仍然比较传统而不够现代,在审美情趣上,传统的田园风情,舒缓的慢节奏,旧文人的雅趣闲情,对亲情和自然的依恋仍然是一种强大社会集体无意识。
或者说,这是我们的心态不够“现代”而支配着我们自然地亲近不够“现代” 朱自清,因而只见其美而难见其瑕。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少大陆学者和读者总是用跪着的姿态仰视名人、伟人,研读名家名作时习惯性地抱学习、崇拜心态而不是对等心态,因而难以发现名家名作之不足。
此外,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中有不少人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他们的研究往往不是从自己的感觉出发而是从教条、从定评出发,体现了一种“注经”式思维。余光中身处较为开放的现代化程度高的台港,欧美文化的修养很深,主业是创作,因而在审视和欣赏现代中国的文学时有更深广的参照系和更现代的趣味。
他对现代散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海峡两岸靠前个重估五四散文价值、破除对朱自清冰心等散文迷信的学人;他致力于现代散文的艺术品格的提高与超越,创造性地把现代西方的多样艺术手法运用了白话散文创作中,并挖掘中国古代散文的魅力;他的散文恢闳恣肆、神采飞扬,文字“有声、有色、有光” ,具有“密度、弹性、质料” ,自成大家。
余先生这篇文章写于70年代,与他评郭沫若、戴望舒等现代名家的文章组成了系列论文。
有趣的是,该文在太原出版《名作欣赏》1992年第2期转载。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与芳香,要真正品尝出它的滋味并非易事。
在这篇“贮满诗意”的“春的赞歌”中,事实上饱含了作家特定时期的思想情绪、对人生及至人格的追求,表现了作家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1927年之后的朱自清,始终在寻觅着、营造着一个灵魂深处的理想世界——梦的世界,用以安放他“颇不宁静”的拳拳之心,抵御外面世界的纷扰,使他在幽闭的书斋中“独善其身”并成就他的治学。
“荷塘月色”无疑是经过了凄苦的灵魂挣扎之后,找到的一方幽深静谧的自然之境,曲折地体现了他“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而“早春野景”则使他的梦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开阔、蓬勃的境地,突出地展示了他要在春天的引领下“上前去”的人生信念。后者自然是前者的延续、**、提升。
但不管这两个世界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源于朱自清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春》确实描写、讴歌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春天,但它更是朱自清心灵世界的一种逼真写照。
细读朱自清的《春》,我不由地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大病初愈的文化人,面对春意盎然的原野,他又重新找回了一种自信和自尊,编织着自己的理想之梦。这是一个经历了“心灵炼狱”的知识分子,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他沉醉其间,诗情联翩,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心灵冲动。
他从时代的“十字街头”撤退下来,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我总觉得,朱自清笔下的“春景图”,不是他故乡江浙一带的那种温暖潮湿的春景,也不是北方城郊的那种壮阔而盎然的春景,更不是如画家笔下那种如实临摹的写生画,而是作家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他的心灵酿造出来的一幅艺术图画。
在这幅图画中,隐藏了他太多的心灵密码。 朱自清研究专家吴周文先生说:“在很多散文中,朱自清惨淡经营诗的意境,将人格美的‘情’与自然美的‘景’两者交融起来,创造了情与景会、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种境界的构思,整个地展现自我人格,以美妙的意象作为人格的外化手段,于是他的笔下,自然美成为自我人格的精神拟态,或象征性的写照;个人特定的情绪、思想,也因自然美的依附,得到了诗意的写照,或者说得到了模糊性的象征。
怎样创造这种意境,完成自然美与人格美二者的附丽与连结?对此,朱自清则是继承弘扬以形传神、重在神似的艺术精神这一整体性的审美把握,加上‘诗可以怨’的审美理想的制导,生成了风格的隐秀与清逸的色彩。
”
(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对朱自清散文的深层意蕴,我以为这些话是深中肯綮的。朱自清属于那种感情和感觉特别敏锐、细腻、真挚的人,对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山水花鸟等等,又有着特有的亲和情怀和观赏兴致。
他的写景,往往是景中有“我”,“我”中有景,景“我”合一。他所以要调动起自己的一切感官以及思想和情感,反复品味、字斟句酌、“用笔如舌”,正是要把自己的全部人生、人格投入到大自然的形神中去,让自然的美与他人生的美浑然为一。
他不像鲁迅,在描写自然中采取一种超然的、审视的态度,甚至不惜写了自然的丑来;他也不像周作人,在刻画自然中沉溺其间、忘却自己,恨不得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朱自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投入的、虔诚的,但同时又是自觉的、清醒的。
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中庸之道”的真谛的。在《春》这篇简短而明朗的散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操守和审美理想。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在朱自清所有的散文中,开篇就写得如此明朗、欢快、昂奋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
这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少年的作文,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精心之作。作者所以有这样一种心境和情绪,一定是因为他走过了一段最阴暗的日子后,找到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他是在借明媚的春光,抒发自己的一种心境。“盼望着,盼望着”,动词的叠用,显得突兀、有力、急切,隐含了他曾经的阴暗、苦闷岁月,以及在那煎熬中对未来的苦苦求索。
现在光明终于降临到了眼前,他怎么能按捺住欢欣鼓舞的心情呢?“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是初春的朦胧景象,但又何尝不是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体验呢? 在作品中,朱自清展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多姿多彩、全方全位的春天。
地上是大片大片嫩绿的小草,田野上是一棵一棵盛开的桃树、杏树、梨树,在如火如荼的花团中,飞舞着成群的蜜蜂、蝴蝶;在晴朗、温馨的天空中,吹拂着软和的杨柳风,氤氲着土香、草香、花香的气息,弥漫着各种鸟儿动听的乐曲,还有牧童嘹亮的笛声……作者在这里把大自然写活了、写足了、写透了,把大自然。
朱自清在《背影》中写他父亲是一个胖子,过铁路线十分的不便,但是仍然坚持要为他买橘子。
那个时候,朱自清已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了,虽然处在兵荒马乱,条件艰苦,有不安全的隐患,但是在父亲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需要关照的孩子。
这种“不能”又“不得不能”的鲜明对比,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到父亲的爱总是那么无微不至,总是那么牵肠挂肚。
也许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总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会产生《背影》式触动。
正是如此,朱自清情不自禁地抓住买橘子这个细节特意进行了描写,那一招一式的动作清晰明了,使人久久难忘,也使作者三次泪盈满眶。
也正是这样一个感动的情节,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使他萌生了以“背影”这样一个动情点,从细节处反映人生的大道理,而写出了表达父爱的传世之作。
希望有帮助。。。。
以上就是朱自清的简短评价(朱自清的根本缺陷)的详细内容,希望通过阅读小编的文章之后能够有所收获!更多请关注倾诉星球其它相关文章!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qsxq.cn/sbzt/bjUaRvCn.html
上一篇:销售三句话留住顾客
Copyright www.qsxq.cn 【倾诉星球】 联系我们 | 皖ICP备2021018307号-4
皖ICP备2021018307号-4
本网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果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